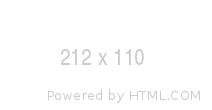
蝎虎座 - 生活在地下世界的爬行動物 - 3。 部分
 18。 04。 2024
18。 04。 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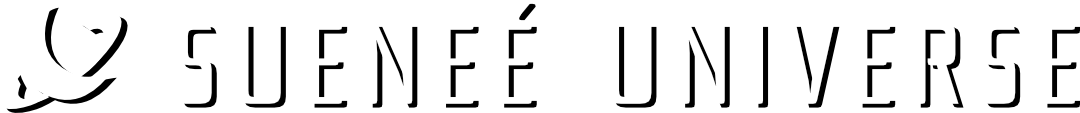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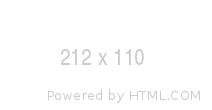
 18。 04。 2024
18。 04。 2024
 1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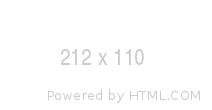
 17。 04。 2024
17。 04。 2024
 6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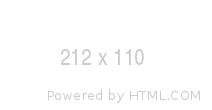
 16。 04。 2024
16。 04。 2024
 8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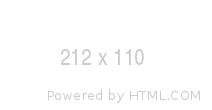
 15。 04。 2024
15。 04。 2024
 18。 03。 2018
18。 03。 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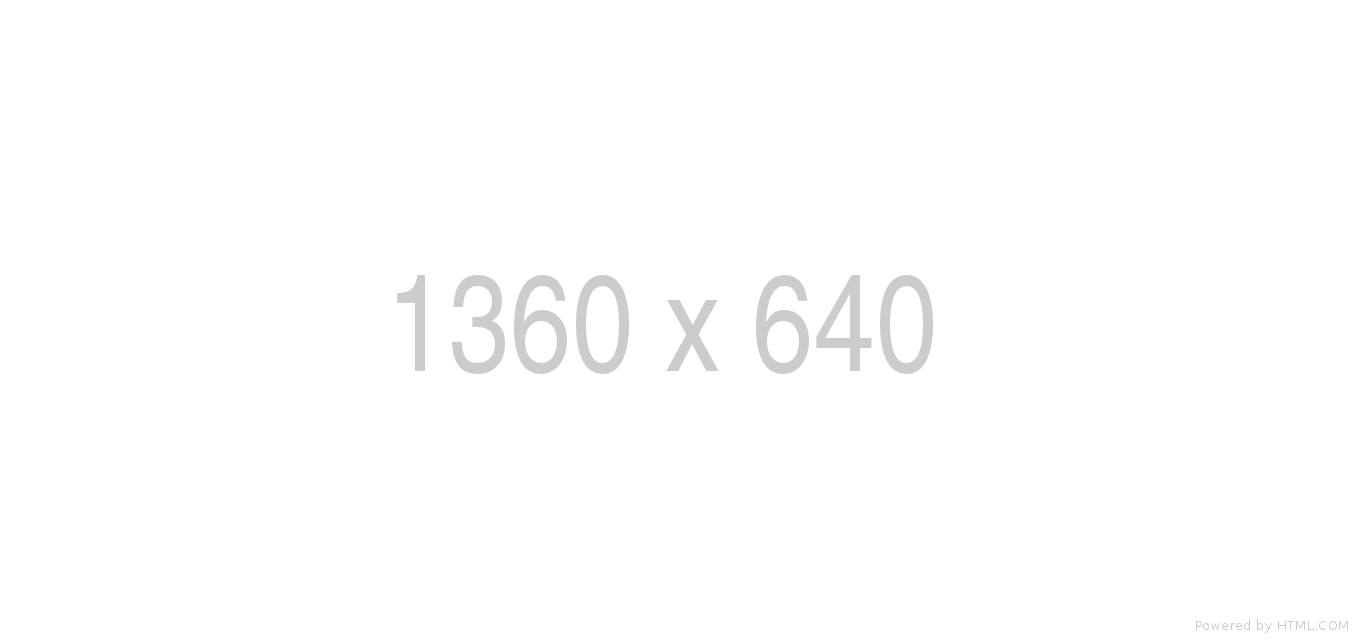
短篇故事 - 一段時間後他請我打電話給他。 這次,我也是懷著忐忑的心情爬上樓梯。 我進入了為恩西姆指定的房間。 門衛帶我去了書房。 他站在窗邊看書。 他讀完,然後把目光轉向我。
「病人怎麼樣了?」他問道,但顯然這不是接下來談話的主要焦點。
我簡單地告訴了他Lu.Gala的病情有所好轉,並補充說不再需要我的服務。 他聽著,保持沉默,點了點頭。 我的眼睛一片空白,想起了我的曾祖母和她在我被送到安娜金字形神塔之前的樣子。
「我發現了一些事情,蘇巴德。 請坐。」他用手示意我該坐的位置。 「我收到了安氏神殿恩斯的訊息。 他不知道誰和你有相同的特徵。 他不認識這樣的人。 但在 Gab.kur.ra 的 Lu.Gal 的調解下,你被接受了,」他停頓了一下。 可以看到他正在積蓄力量準備接下來要說的話:“蘇巴德,那個人很可能是你的祖父。”
它把我迷住了。 事實上,祖母從未談論過她女兒的父親。 我突然明白為什麼當那個男人來拜訪我們時她不在屋子裡。 如果他有和我一樣的能力,那麼他一定是阻止安娜神殿思想之戰的人。 我沉默了。 我思考了關於我的家庭我並不真正了解的事情。 我從來沒有想過為什麼這兩個女人都沒有男人生活。 當我再次回家時我必須問這個問題。 家——這個字突然因渴望而刺痛。
恩西看著我。 他結束了我們的沉默:「Lu.Gal 告訴我你對 Urti.Mašmash 感興趣。 我可能有東西要給你。」他示意我跟他一起去。 他打開圖表架,架子後面出現了一座樓梯。 他對我的驚訝笑了笑,並補充說:「這樣更快,但不要向任何人提起。」他拿了燈,我們下了樓。 我們沉默了。 恩西出於考慮,而我……除了不久前收到的關於一個名叫 Gab.kur.ra 的人的信息之外,我仍然無法正確地將我的思緒集中在其他事情上。 我們到達了另一扇門。 一扇帶有新月標誌的金屬門。 恩西打開門,打開了裡面的燈。
我們站在金字形神塔下方的廣闊空間。 在充滿桌子、雕像和設備的空間。 每個房間都被一扇厚重的金屬門隔開,與入口相同。 我環顧四周,感到很驚訝。
「檔案。」恩西簡潔地說,帶著我穿過房間。 然後我們停了下來。 「就是這裡了。」門上裝飾著恩基的徽章。 「你也許會在這裡找到你想要的東西,」他微笑著說。 然後他嚴肅起來。 「舒巴德,這裡隱藏著什麼,是人們看不到的。 禁止進一步傳播這裡隱藏的知識。 別問為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們只是管理者。」房間裡擺滿了用祖先語言寫的桌子。 在我面前的是一筆驚人的財富──幾個世紀以來累積的知識。 我正在瀏覽清單,忘記了恩西和我在一起。
「舒巴德……」他靠在我身上,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我一定是太全神貫注於清單而沒有聽到他的聲音。
「對不起,偉大的恩西。 我沒聽。 我對這裡存放的桌子數量感到驚訝。 我再次表示歉意。”
他笑了。 他的眼神裡既有善意,也有玩味。 「今天沒有必要做所有的事情。 來吧,我會告訴你地下的其他入口,這樣你就不用每次需要東西的時候都去問圖書館員了。 但請小心。 桌子很舊,其他人不允許進入這裡。”
於是我就到地下檔案館去找。 桌子越舊,就越有趣。 他們洩漏了秘密。 就好像人們正在忘記——幾個世紀、甚至幾千年收集的文字和知識的原始含義正在丟失。 新的東西被創造出來,但舊的東西不再被使用,因此工藝因可以使用的東西而變得貧乏,並重新發現了曾經被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
我們經常和 Lu.Gal 討論這個問題。 我很欣賞他的善良和他處理每一個問題的智慧。 我在那裡發現了舊桌子。 太老了,連盧加爾都沒有足夠的年齡來閱讀這些舊記錄。 在埃里德,只有少數人懂得這種早已消亡的語言和早已被遺忘的文字。 其中之一是恩西,但我不敢向他尋求幫助。 我試著學習我能學到的知識,但如果沒有適當的知識,我幾乎沒有機會根據需要管理翻譯。 神話的世界,古老文字的世界,古老知識的世界-有時令人難以置信,正在離我而去。
我還發現了許多老阿祖使用過的食譜,但如果沒有適當的語言知識,就無法確定植物或礦物質的正確識別。 最後我向Sin求助。 他的語言天賦可以加快事情的進展。 不幸的是,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從來沒有問過我帶來的圖表是從哪裡來的。 他從來沒有問過我連續幾天消失到哪裡去。 當我需要幫助時,他從不抱怨。 但即使是他也缺乏舊手稿。
最後我還和Lu.Gal討論了向恩西請教的可能性。 他認為這是個好主意並為我預約了。 恩西並沒有反對──相反,他先安排我去E.dubba──桌子之家的老Ummii那裡上課,他教我古語言的基礎知識。 他親自幫我翻譯。 這讓我們更加親近。 它使我們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在我難得的短暫空閒時間裡,我想起了來自 Gab.kur.ra 的那個人,但我一直推遲寫給祖母的信。 我安慰自己,回家後親自和她談談這件事會比較適合。 命運為我決定了另一件事。 戰爭已經開始了。
我坐在Lu.Gala的房間裡唸一些翻譯給他聽。 我們時不時地談論一些段落。 雖然沒有我們希望的那麼頻繁,但那是令人愉快的時刻。 就在這寧靜的時刻,霧氣再次出現在我的眼前。 安娜的金字形神塔痛苦地尖叫。 一條隧道出現在我的面前,人們正在裡面行走。 我認識和不認識的人。 其中就有寧納瑪倫。 他們臉上的表情不是和平與和解,而是恐懼。 巨大而痛苦的恐懼。 那種恐懼讓我起雞皮疙瘩。 Nennamaren 試著告訴我一些事情,但我不明白。 嘴裡說出了我沒聽見的話。 我尖叫。 然後黑暗來臨了。
當我醒來時,他們都站在我身邊——Ensi 和 Lu.Gal。 兩人都害怕了。 這次我不得不大聲尖叫。 僕人送來了水,我狼吞虎嚥地喝了下去。 我的嘴巴很乾,鼻子裡有燒焦的味道。 他們都沉默了。 他們無語地看著我,等著我說話。 我只說了一句:「戰爭。」我發現自己又到了隧道的邊緣。 祖母。 「不,奶奶,不!」我在心裡尖叫。 疼痛佔據了我身體和靈魂的各個部分。 我陪她穿過隧道的一半。 她回頭看了一眼。 她的眼睛充滿悲傷,臉上掛著淡淡的微笑,這對我意味著:“快跑,蘇巴德”,她的嘴唇說。 然後一切都消失了。
「請醒來,」我聽到恩西的聲音。 「醒醒吧!」他的淚水落在了我的臉上。 我躺在Lu.Gala的床上。 恩西牽著我的手,盧加爾在門口接信差的消息。
「戰爭。」我輕聲說。 「跑步。 我們得走了。」我的頭在旋轉。 我試著從床上坐起來,但身體還是很虛弱。 我把頭靠在恩西姆的肩膀上。 我哭不出來。 我的意識拒絕接受關於我祖母去世的消息,關於我出生和度過童年的城市裡的人們的死亡的消息。 我知道我們必須走了。 每當某個地方發生戰爭時,他們都會先攻擊寺廟。 這座城市所有的財富都聚集在那裡。 為了削弱行動能力,金字神塔的代表被無情地殺害。
 露加爾悄悄地向我們走來。 他輕輕觸碰恩西。 他對自己看到的這一幕感到有些尷尬,但沒有發表評論。 他抱歉地看著我,說:“現在不行。” 必須召開理事會。 必須清理神廟。 」恩西的手鬆開了。 他輕輕地將我放回床上。 「去吧,」盧加爾說,「我派人去找辛了。」他在我旁邊的床上坐下來,握住了我的手。 他沉默了。 他的眼中充滿了恐懼。 我試圖阻止那些攻擊我的感覺。 這讓我筋疲力盡。 然後辛進來了。 他來找我。 他什麼也沒問。 他打開醫療包。 「你必須睡覺,舒巴德,」他看到我時說。 “我這就給你轉移。”
露加爾悄悄地向我們走來。 他輕輕觸碰恩西。 他對自己看到的這一幕感到有些尷尬,但沒有發表評論。 他抱歉地看著我,說:“現在不行。” 必須召開理事會。 必須清理神廟。 」恩西的手鬆開了。 他輕輕地將我放回床上。 「去吧,」盧加爾說,「我派人去找辛了。」他在我旁邊的床上坐下來,握住了我的手。 他沉默了。 他的眼中充滿了恐懼。 我試圖阻止那些攻擊我的感覺。 這讓我筋疲力盡。 然後辛進來了。 他來找我。 他什麼也沒問。 他打開醫療包。 「你必須睡覺,舒巴德,」他看到我時說。 “我這就給你轉移。”
盧加爾搖搖頭,“請把她留在這裡吧。” 這樣比較安全。 留在她身邊。 我現在得走了。'
他給我倒了一杯酒。 當我試著握住碗時,我的手在顫抖。 他接過湯匙,抬起我的頭,一小份地給我喝了飲料,「發生了什麼事,蘇巴德?」他問道。
「戰爭。 戰爭已經從我們這裡開始了。」他的臉色變得蒼白。 他知道士兵們抵達埃里德只是時間問題。 他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誰?”他問,我已經半睡半醒,回答他:“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我突然醒了。 有什麼東西把我從夢的懷抱中拉了出來。 我的上方是地下的天花板和辛的臉。
「終於,」他說。 「我開始害怕了。」牆壁在角落迴響,我脖子後面的感覺越來越強烈。 我猛地坐了起來。 我不得不睡很久。 我很虛弱。 我的嘴唇因口渴或發燒而乾裂,但死亡的感覺卻異常強烈。 辛扶我站起來,帶我走向他。
「恩西! 我親愛的恩西。」我在心裡尖叫。 當生命離開他的身體時,他的孩子卻在我體內成長。 我雙手捧著他的頭,努力回想我們在一起的時光。 我想起了太陽,想起了被風弄得渾濁的運河裡的水,想起了在檔案館裡度過的時刻,想起了我們雙手相握的時刻。 隧道開通了…
我慢慢地閉上了他死氣沉沉的眼睛。 罪擁抱了我,我淚流滿面。 他像個小孩一樣安慰我。 然後他開始唱一首歌。 母親過世時,父親唱的這首歌。
「他不想離開你,」他告訴我。 「他把他們都打發走了,然後留下來了。 祂把我們藏在地下,並親自保衛我們的藏身之處直到最後。 我發現他太晚了——來不及救他了。
我們跑過地下通道。 「跑到 Gab.kur.ra,」恩西說道,於是我們試圖進入被士兵圍困的城市之外的地下。 Sin所準備的治療師的衣服足以保護我們。 到處都有人,到處都需要治療師。 我們有希望。
發燒三週後我恢復得很快。 唯一讓我擔心的是孕吐。 我試著向辛隱瞞我的狀況,儘管我事先就知道這是徒勞無功的。
旅途變得越來越艱辛。 我們走過一片沙石景觀。 晚上和早上還可以去,但下午太熱了,所以我們就想辦法找個地方避暑。
有時我們會遇到來自山區或沙漠的遊牧部落。 他們大多對我們很友善。 我們用我們的藝術回報他們的幫助。 我們沒有在任何地方停留太久。
我懷孕的時候很艱難。 辛沒有說話,但看得出來他很擔心。 最後,我們到達了我們所希望的可以休息一會兒的地區。 這裡的土壤相當肥沃,河邊有足夠的定居點,保證我們不會挨餓,也有足夠的工作給我們。
我們租了定居點邊緣房子的一部分。 起初,我們周圍的人都難以置信。 他們不喜歡外國人。 定居點內部存在著緊張和怨恨。 大家互相注視著,逐漸同時成為了囚犯和看守。 言語、手勢不但不能讓他們更親近,反而會傷害他們。 敵意、恐懼、懷疑——所有這些都影響了他們的生活和健康。
最後,又是疾病迫使他們容忍我們在那裡。 人類的痛苦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 無論是肉體的痛苦,或是心靈的痛苦。
「我們需要談談,舒巴德,」有一天早上他說。 我等待這次談話已經很久了。 我焦急地等待著她。 我正在準備早餐,所以我只是看著他點點頭。
「你必須做出決定,」他說。
我知道我們不能在這裡久留。 雖然我們在這裡並沒有遇到危險,但定居點的氣候並不適合,讓我們倆都筋疲力盡。 我們也開始感覺到我們的每一步都在被監視,每一個動作都受到最嚴厲的評判。 這已經足夠了——一個無法治癒的病人,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的目的地還很遠。 我們前面還有一條漫長而艱辛的路。 我的懷孕過程並不順利,我不知道我能否在途中為孩子提供至少起碼的條件。
我知道我必須做出決定。 我很早就知道了,但我一直推遲我的決定。 孩子是我在恩西姆之後所剩下的一切——事實上,如果你不算辛的話,我就只剩下一切了。 我不知道埃利特是否還活著。 我不知道那個可能是我祖父的人是否還活著。 我們不知道一路上等待我們的是什麼,找到一個可以長期定居的地方的希望也微乎其微。 我必須盡快做出決定。 懷孕持續的時間越長,風險就越大。
Sin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 「今天就待在家裡,放鬆一下。 我會停止為我們兩個工作。」他微笑著。 那是一個悲傷的微笑。
我走到屋外,在樹下坐下。 我的思想告訴我,現在不是把孩子帶到這個世界上的好時機,但我內心的一切都反對它。 我把頭靠在樹上,思考如何擺脫這種困境。 戰爭、殺戮、破壞。 在那之後,會有一個舊的將被遺忘的時刻——數個世紀積累的知識,知識和經驗將慢慢消失,一切超出他們以前經驗的事物都會被懷疑。 每場戰爭都會伴隨一段無知的時期。 力量是被挫敗的,而不是為了破壞和防禦而創造的。 恐懼和懷疑,保護自己和他人——世界將開始像這樣的解決方案。 不,現在不是帶孩子來到這個世界的好時機。
然而,我內心的一切都違背了這個邏輯結論。 這是一個孩子──他的孩子。 一個男人,一個應該被剝奪生命的人。 治療師的工作是拯救人的生命,而不是毀滅他們。 我無法決定,但我必須這麼做。 然後是罪。 這一刻,我的生活與他的生活交織在一起。 我的決定也會影響他的生活。 我把手放在肚子上。 「你總是有機會探索自己的情緒…」Lu.Gal 告訴我。
一股寒意開始從他的背脊升起。 孩子知道我內心在想什麼,用恐懼來反擊。 它一邊呼喚一邊哀求。 然後一切開始陷入熟悉的迷霧中,我看到了我的女兒和她的女兒以及他們女兒的女兒。 他們所擁有的能力既是詛咒也是祝福。 他們中的一些人站在柴堆上,火焰吞噬了他們的身體。 譴責的話、誤解的話、判決和譴責的話。 殺死的話。 “巫婆。”
我不知道這個詞——但它嚇到了我。 我看到那些被我的子孫之手所幫助的人的眼神——充滿恐懼的眼神變成了寬慰。 甚至那些自身恐懼的人的表情也引發了譴責的風暴並導致了殘酷。 我的恐懼與喜悅交織在一起,我的恐懼戰勝了決心。 我把手放在地上。 大地一片舒緩。 即使這次經驗也沒有幫助我做出決定。 它只會強化我的感覺:儘管我看到了一切,但我沒有權利殺人。
我自己的生活充滿了困惑和我的能力所造成的痛苦。 我沒有艾利特的快樂,也沒有曾祖母的力量,但我仍然活著,並且想要活著。 所以我決定了。 我沒有權利讓Sin靠近並減少他實現目標的機會。 我沒有權利奪走未出生的生命。 它將被稱為Chul.Ti——快樂的生活。 也許她的名字會帶給她艾利特的快樂,生活對她來說會更容易忍受。
辛在傍晚時分又累又累地回來了。 他沒有堅持要我告訴他我的決定。 當他終於看向我時,我從他眼中看到了愧疚。 因強迫我做出決定、帶給我痛苦而感到內疚。 棕色的眼睛充滿了恐懼,一度充滿了喜悅。
「他的名字叫 Chul.Ti,」我告訴他。 「我很抱歉,Sin,但我無法做出其他決定。 和我在一起很危險,所以你一個人去 Gab.kur.ra 可能會更明智。」他微笑著,那一刻我明白了他要結束自己的生命是多麼困難。
「也許這會更明智,」他思考道,「但我們一起開始了這段旅程,我們也將一起完成它。 也許Chul.Ti會為我們的生活增添一些歡樂,帶給我們幸福。 你給了她一個美麗的名字。」他笑著說。 「你知道,我很高興你做出了這個決定。 我真的很高興。 但我們不能留在這裡。 我們必須快速前進。 我們需要找到一個更方便的地方讓你把她帶到這個世界上。 Gab.kur.ra 還是太遠了。”
我們買了一輛馬車,這樣我們就可以帶著我們製作的藥品、工具和設備、基本裝備和旅行用品。 我們的設備還包含新的表格,我們在晚上把這些表格寫下來,這樣所獲得的知識就不會被遺忘,從而使知識能夠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我們默默地繼續我們的旅程。 我問自己Sin是否後悔與我分享命運的決定,但我不能直接問他。
旅程並沒有像我們希望的那樣快進行——部分原因是我懷孕了。 我們走過的風景比家裡更加多樣化,而且充滿了障礙。 因為有動物,我們必須選擇一條能為它們提供足夠食物的路線。 這裡人煙稀少,我們常常好幾天連一個活人都沒見過。
最後我們到達了一個小定居點。 用泥土加固的蘆葦小屋圍成一圈。 一位女士朝我們跑來,示意我們快點。 我們達成了和解。 Sin跳下馬,抓起藥袋,朝女人指的小屋跑去。 然後她扶我下來。 我想要跟著辛,但那個女人阻止了我。 標誌表明不建議進入小屋。
罪出來呼喚我。 定居點的人試圖擋住我的路。 這不是一個好的開始。 辛試著用他們的語言告訴他們一些事情,但從他們的表情來看,他們顯然聽不懂。
一個騎馬的人似乎正在向我們走來。 他駕駛一架噴射機。 他下了馬,環顧四周,聽到了男人們憤怒的聲音,然後轉向辛,「你為什麼要讓那個女人進入男人們的房子?」他用我們能聽懂的語言問道。
“她是一位治療師,”辛回答道,“我需要幫助來拯救病人的生命。”
「這裡沒有女性參觀男性專用場所的習俗,」騎手回答道,難以置信地看著我。
罪惡因憤怒和煩惱而漲紅了臉。 我示意他冷靜下來,然後再說話。
「看,」他告訴他,抓住那人的手肘,把他帶到一邊。 「那個男人病得很重,想要治療他,不只需要她的幫助,還需要其他人的幫助。 剩下的時間不多了。 他需要進行手術,而且必須在乾淨的環境中進行。 這些人是否能夠清理乾淨並為我們的工作騰出空間,或者我們應該將這些人轉移到其他地方?
那人想了想,然後用他們的語言對旁觀者說了幾句話。 定居點的人們分開了,騎手示意我進去。 他就跟我們一起去了。 裡面的空間很大,但是很暗。 那人躺在墊子上,呻吟著。 他的額頭上冒出了汗。 一股寒意開始從我的脊椎升起,我的下腹出現了熟悉的疼痛。 我看著辛點點頭。 他轉向騎手,解釋瞭如果他康復了將會發生什麼。 他仔細地聽著。
我環顧房間。 她不適合接受手術。 地板很髒,而且很黑。 我們需要一張桌子、水、乾淨的布。 我走近那個男人。 他受苦了。 疼痛折磨著他,他咬緊牙關努力忍住。 這讓他筋疲力盡。 我打開包包,拿出本來可以緩解疼痛的藥。 我給了他一杯水,雙手捧著他的頭。 他連反抗的力氣都沒有了。 騎手停下來,疑惑地看著我。 我閉上眼睛,放鬆下來,試著回憶起平靜的景象,海浪拍打著海岸,清新的微風輕輕地搖晃著樹冠。 男人平靜下來,開始睡著了。
騎手走了出來,開始向定居點的人們發號施令。 男子被抬了出去,地板被灑了水並打掃。 他們把桌子搬來,把它們敲在一起並清理乾淨。 西姆正在準備工具。 病人睡著了。
這時,一位老人走了進來。 他悄悄地進來了。 我背對著他站著,準備好一切必要的事。 一種依偎在我脖子後面的感覺讓我轉過身來,我轉身去看他。 他的眼神裡沒有惡意,也沒有憤慨,只有好奇。 然後他轉身走出小屋,對著騎手喊了一聲。 他們一起回來了。 他們越過了辛,來到了我身邊。 嚇到我了。 擔心我的存在會導致進一步的複雜化。 老者躬身行禮,說了幾句。
「他說他想幫忙,」騎手翻譯道。 「他是當地的治療師,擁有可以加速傷口癒合和預防發炎的植物。 女士,他很抱歉打擾了,但他認為他可以提供幫助。
辛停下手中的工作,交替看著老人和我。 我也鞠了個躬,請那人解釋一下植物及其萃取物的功效。 我感謝他提供的幫助並請他留下來。 我很驚訝他竟然對我說話,但我沒有發表評論。 騎手翻譯。 如果他的藥能起到老人所說的作用,對我們會有很大幫助。 辛請老人家準備他認為合適的東西。
他們帶來了一個男人。 我命令他們把他脫光。 眾人疑惑地看著,但最終還是執行了命令。 我開始用準備好的水和溶液清洗那個人的身體。 老人準備好了藥物,辛則向他展示了該用在他身體的哪個部位。 手術已經開始。 辛乾得很快,而且憑藉自己的精湛技藝。 一名騎兵站在入口處,阻止好奇的人進入並進行翻譯。 他臉色蒼白,但仍堅持著。
我被病人的情緒攻擊了。 我的身體痛苦地尖叫著,我努力保持清醒。 然後老人做了一件我沒想到的事。 他用溶液在水中清洗雙手,將手掌放在我的額頭上。 他吸了一口氣,慢慢地開始透過鼻子呼出空氣。 我的感情開始消退。 我感覺到了情緒,但我沒有像我一樣感受到這個男人的痛苦。 這是一個巨大的解脫。 他用一堵無形的牆將我的感情與那個人的感情隔開。 我們繼續。
老人並沒有乾涉──相反,他像一位經驗豐富的外科醫生一樣協助辛。 在使用藥物之前,他總是詢問Sin。 我們完成後,合上老人的腹部,塗上老人的萃取物(據說可以加速傷口癒合),然後包紮他。 我開始在他身上塗抹油藥,據說可以增強這個人的體力,讓他沉睡一段時間。 我眼睛很痛。 兩個人的眼睛也都因疲勞而紅了。
入口處的騎手依然臉色蒼白。 參加手術使他變得虛弱。 我走到他身邊,抓住他的手,帶他往外走。 我把他放在樹下。 我一如既往地將雙手放在他的後腦後,伴隨著咒語,以打圈的方式讓他平靜下來,讓他入睡。 老人從小屋走出來,下達了命令。 他們開始工作。 然後他走到我身邊,示意我跟他走。 我在男人們的眼中看到了寬慰。 我不明白,但我遵守了他給我的指示。
他帶我到村子邊緣的一間背對圓圈的小屋。 一個比辛年紀稍小的少年出來迎接他。 他的右腿已經變形。 他一瘸一拐的。 他們把我安置在外面,男孩就消失在村子裡了。 當他回來時,他的懷裡捧滿了鮮花。 他消失在小屋裡。 老人坐在我旁邊。 他渾身散發著冷靜和沈著。 年輕人走了出來,做了個手勢。 老人示意我繼續坐著,進去吧。 過了一會兒,他邀請我進去。
小屋的中央,有一圈男孩帶來的植物,角落亮著燈,散發著醉人的香味。 他指示我脫掉衣服。 我尷尬得臉紅了。 他微笑著送走了年輕人。 他本人背對著我。 我脫掉衣服,赤裸裸地站在那裡,肚子鼓鼓的,肚子裡的寶寶正在長大。 老人轉身示意我進入圈子。 他的嘴裡發出悠揚的話語,他的手輕輕地撫摸我的身體。 他用水在我的皮膚上畫畫。 我不明白。 我不知道他舉行的儀式,但我尊重他。 我信任這個人,在他面前感到安全。
他舉行了淨化儀式。 我是一個進入男人領地的女人,所以我必須被淨化,就像我進入的小屋必須被淨化一樣。 能量不能混合。
男孩帶來了衣服。 定居點婦女穿的衣服。 他把他們放在我旁邊圍成一圈,兩個人都離開了,這樣我就可以穿衣服了。
我出去了。 罪站在入口處,小聲地和騎手說話。 他轉向我,“我們會留在這裡,蘇巴德。”
一個老人和一個男孩正在一個男人家裡進行淨化儀式。 我又累又昏昏欲睡。 也許是帳篷裡的燈籠裡飄來的醉人的味道。 我的眼睛還是腫的。 辛看著騎手們,在他們帶我走向小屋時抓住了我的手臂。 他和我一起走進去,一位老婦人正在那裡等我們。 他們把我放在準備好的墊子上。 Sin靠在我身上,「現在睡吧。 我們在這裡很安全。」然後他們都離開了帳篷,我精疲力盡地睡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