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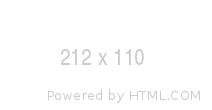
用mions檢查金字塔
 19。 04。 2024
19。 04。 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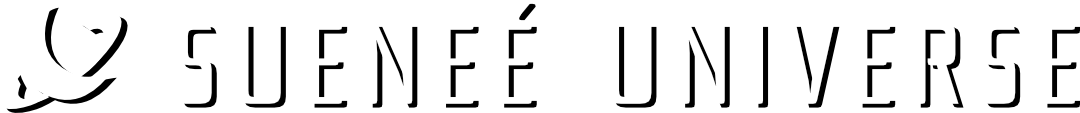


 4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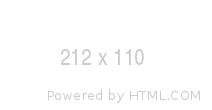
 19。 04。 2024
19。 04。 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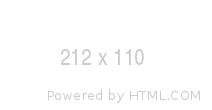
 18。 04。 2024
18。 04。 2024
 1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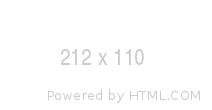
 17。 04。 2024
17。 04。 2024
 6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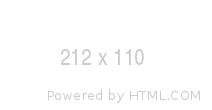
 16。 04。 2024
16。 04。 2024
 15。 07。 2013
15。 07。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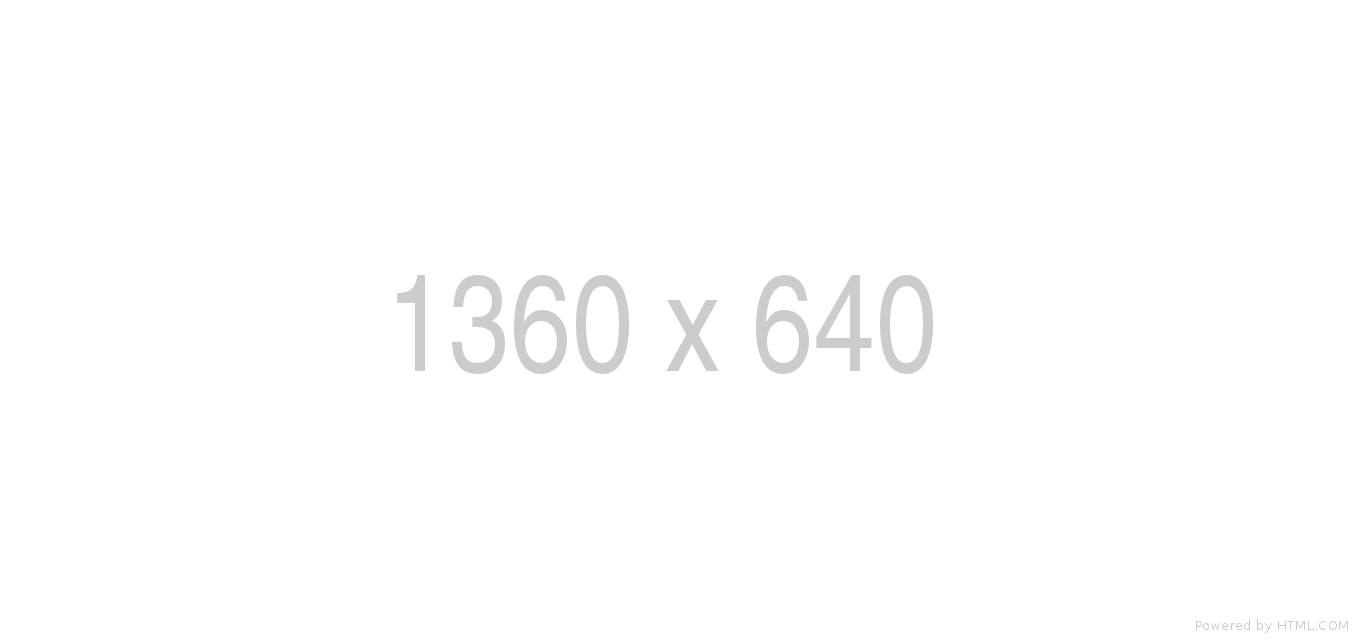
那一天,我是在大約三十英里的腳。在路上,我在曙光森林Klohariánskými才走了出去。 我已經做了五六天,並簽署了我的條件。 這些誰載Kulahů,基本上帝國內的一種主權國家的認識界限,為什麼讓那些最難到達的地方。 如果他的旅行期間在陡峭的山峰,廣湖泊,洶湧的河水,鋸齒峽谷進來,或在我的情況下,堅不可摧的森林,你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們背後,你會發現一個國家比一個更加古怪其中如此慘重這裡。
當他想到這件事時,他幾乎說道,彷彿大自然本身想要這樣的國家分裂。 但那隻是一個轉彎,因為實際上沒人能想到它。 為了得到這樣的想法,他需要一張地圖。 而且也可能僅僅是因為她必須首先創建一個和所有的這些作品在腸子Luniciánské章,中間Tukatuše,我們明君的住宅資本被小心保護。
但是,“ Tukatush”僅是源自舊語言的通用名稱。 正式地,大都會對自己的稱呼有所不同,但沒有一個普通百姓知道或接受,因為無名者(即窮人)使用貴族言論受到了懲罰。 照常切出舌頭。 這比拿著地圖挖眼睛或複制地圖(眼睛和手)要輕一些,但即使這樣,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也可以不玩那些不是在玩地圖的遊戲。 從邏輯上講,這有點胡說八道,因為崇高的演說是如此復雜,名字如此笨拙,以至於沒有人顯然不需要處理它。 但是,秩序是秩序,而保持固定的層次結構是最嚴重的問題。
就地圖而言,最初,雙眼都在復印,但這樣的人不能很好地工作並納稅。 根據社會專家的研究,他的生活處於效率的邊緣。 專家們,正如他們自己所稱的那樣,大多是屬靈的,因為他們通常沒有任何事情可以證明是有用的。 鑑於以他們的智慧進行調試的政府壓制了一切不會帶來繁榮與繁榮世界的事物,目擊者的法律得到了修正。 一方面,這個男人仍然比雙手不成比例地工作得多,但沒有眼睛。 他沒有為腿付錢。
我有機會看到曾經看過的地圖,確實是地圖。 事實上,我研究了她。 我必須。 我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在一個鎖定的,但光線充足的房間裡,記住她的每一個細節。 城市,要塞,它們的名稱,路徑,邊界,它們之間的距離以及所有地形。 地圖研究的房間是秘密的,被稱為地圖室。 這是唯一的完整和完整的地圖,它是巨大的。 房間很大,因為如果不是,觀察者只會看到底部邊緣。 需要一段距離。
由於保密的質量,任何地方都沒有窗戶,但燈光像中午一樣。 關於這一現像我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沒有解釋。 在石頭地板的中間是一件由深紅色地毯和枕頭組成的單件家具。 他們已經擴大了。 在一個很遠的角落裡,在廁所對面的角落裡有一個雙層大門。 進入房間一生只有一次,隨著她的遺棄,一個毫無生氣的保密的承諾被強加給你,否則你知道是什麼。 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通常沒有太多的調查空間。
我很清楚,那天我不會來。 眼睛看到,一個和平,潮濕的山坡蔓延。 我讚賞這一次,我的旅程將我帶到草地和其他綠色植物在地上生長的地方。 太陽落在右邊的一座小山上,我再次意識到我餓了很多。 我從森林中出來的時候並沒有遇到過單一的解決辦法。 在途中,我遇到了只有幾個孤獨的定居點,主要是牧民,但他們遠遠不能回來。
在我完全沉默之前,我想知道是否可以在人類住所謀生。 我坐下來說我會冥想它。 畢竟,有黃昏,因此是我們的主,一個唯一的,全能的創造者和生命保護者 - Hulahulaukan必須祈禱的時刻。
所以,我自然而然地用文字和謙卑來平靜我的思想,以便它可以與神聖的智慧合併,讓我看到正確的方向。 然後,我起身繼續直行。
我不再需要兩個小時放棄感謝的話。 我在地平線的黑色曲線上看到一道小小的橙色光芒。 彷彿在那個距離,他聽到了木頭爆裂,水壺在火上冒了出來。 我越過了我面前的高地,寒冷的溪流和身後的陡峭山谷,衝上了大樓。
當我能分辨出屋頂上的煙霧和房屋的深色輪廓時,我減速了一步。 畢竟,朝聖的基本規則之一是:“你永遠不知道誰在看。”這在聽覺和感覺上也是如此,但是第三條並沒有說太多。
有幾個聲音從腸子裡。 至少有一個是女性,這通常是一個好兆頭。 在我敲門前,我看了一眼房子。 那是另一個規則。 然後我聽了。 裡面好像心情很好。 儘管我很短的時間內無法確定談話的主題,但並不涉及任何暴力或可疑的事情。 我發表了我最信任的表達方式,並用一塊厚厚的木板反复敲擊棍棒的末端。 典型的聲音消退。 然後是隱隱約約的沉默和推力,過了一會兒,門打開了。
燈首先伸出,然後是手臂,然後是頭部。 是那個女人。 她的頭髮堅硬乾燥,頭髮隨意地往後拉。 “旅行者?”她說,從上到下測量我。 “你是和尚嗎?”
“是的,女士,寧靜的夜晚! 一個流浪的和尚正在尋找今晚的庇護所和一些東西。 我坐著沉思,天意把我帶到了你家門口。
“那真是天意!”她笑了。 “歸根結底,和尚給屋頂帶來了祝福,帶來了主的微笑。 甚至有一個豐滿的願望,“她舉起另一隻手的食指出現”(如果他有恩典的話)。
我給予了我的尊敬。
“距離上一個和尚過去已經幾個月了!”她繼續說道。 然後她放鬆了熱情,睜大了眼睛。 “希望你給我們帶來祝福。”
“我帶來了,空腹很難保佑。 它沒有適當的力量。”
那個女人笑了,終於邀請了我。
黃燈擋住了我的溫暖潮流。 火焰的火焰已經耗盡了未結合的石牆。 壁爐在房間的中間,鋪著鋪好的地板,四個男人和另一個女人坐在它周圍。 我打招呼了
鞠躬。 我問:“我可以把它放在隔壁嗎?”但他沒有等答案。 我從肩膀上掉下旅行外套,將手杖靠在牆上,然後將一個更大的較重的袋子掛在掛釘上。
“當然!”將燈放在壁架上的女主人叫道。 然後她從架子上拿了一個木碗,走近壁爐。 她從一個大鍋中取出濃稠的熱混合物,並將其交給我。
“拜託,拜託,和我們一起坐!”當我感謝我的食物時,他們互相邀請我。 我把小袋子滑到背後,坐下。
“今天看起來像是一家精選公司!”其中一個笑了。 “讓我介紹一下我們。 我們可能只是個普通的未具名,但我們仍然知道什麼是合適的! 他一個農民地介紹了一個從附近村莊來的牧民,木匠和一個女人,並親自作為石匠。 女主人是他的妻子。 我通常會刪除名稱,因為我知道我不需要它們。 沒有人期望禮拜堂的代表來講未命名的名字。 但是,這並沒有減少他們向國家組織的代表提供有關自己的信息的義務。 實際上,應該詢問任何信息。
我站起來,看上去很友好。 “而且我是一個旅行和尚。 Bulahičr我的名字並不重要,“我謙卑地補充。 “今晚我很高興和你在一起。”
“太好了!”苗條的金發木匠妻子喊道。 “我以前從未見過流浪的和尚! 您在旅途中是否有很多冒險經歷?“木匠將肘部伸入她的手肘,這樣她就不會受到不敬,但她沒有註意。 “在更廣闊的地區發生的事情幾乎不會給我們定居者帶來。”
“我環遊世界,參觀朝聖的地方,並為上帝和教堂的謙卑服務而接受培訓。 我在需要它的地方提供幫助,如有必要,我會教其規則。 我可以治愈身體,撫平精神疾病。 但是,我可能會讓您熱切的耳朵失望。 在途中,我主要遇到野生動物,在這里和那裡的買家。 我多年前離開首都,繁榮昌盛,毫無疑問,它在我們開明的君主手中繼續繁榮昌盛。 縣之間的貿易流,田間誕生和果園盛開。 捍衛者穿越該國,並在必要時進行干預。 至少三百年來有土匪和爪子。 我只能聽到,但是因為我一個人
沒有受到打擊,我沒有理由不相信。 我們生活在幸福的時代,我們應該為此感到感激!”
一個農民,一個留著鬍子的皺巴巴,瘦弱的傢伙進入了談話。 但是,他沒有從火上抬起頭。 “北部荒地的野蠻人呢? 他們只是消失了嗎?”
“他怎麼知道?”我的頭閃爍著。 帝國北部的州確實對他們有問題。 未知的部落迅速準確地入侵了內部。 它們不僅攜帶農作物和牛,而且變得越來越大膽。
我停頓了一下:“這些步驟有一天可能會將我引向外邊界。” “那隻是引起我們的注意。 防禦要塞上的船員的定期增援部隊向北流動。 我毫不懷疑,邊界是安全的,而且帝國的防禦能力很強。 沒有理由擔心!”
“有人喜歡醃製的蔬菜嗎?”石匠的妻子在刀聲停止時轉離櫥櫃。 “我為這種罕見的場合鍛造了幾副眼鏡。”這份報價得到了熱烈的歡迎。
我要求開放,並要求他們不要以我的存在破壞我的存在。 我靜靜地享受著美食,聽著他們的談話。 他們談到了普通人生活中的許多平庸,並且他們詆毀他們的手藝和鄰居的誹謗。
數十分鐘無聊的八卦後,我舉起手來,“朋友們,夜晚已經過去了,如果不喝點好酵母,那會是多麼有趣的事情!” 我把手伸到腰上,搖了搖晃,液體濺出的泛黃的葫蘆。 “我從遠處抱住她。 Turukus行政長官Rovahorín送的禮物。 “你不知道我在說誰嗎? Turukuss是鄰國的首都,位於Kloharian森林以南數百英里處。 當您與我分享您的非凡飲品時,我想與您分享!”
“我不知道,”木匠跳到板凳上,“允許和尚喝酒!”從丈夫那裡又一次戳了戳。
“當他們來到我們這裡時,有必要接受主的恩賜。 它們是他熱情好客的象徵。 如果沒有什麼可以溫暖您的,那麼寒冷仍然是道路上最強大的敵人之一! “我離開了教堂的舒適和溫暖,這樣我才能更好地服務,並了解到有時為了個人的利益,有必要採取各種措施才能生存。
我舉起食指。 “如果你不告訴我,我不會告訴你。”我微笑著。
“你不會說什麼?”石匠抬起一頭受驚的濃眉。 我環顧四周,深吸了一口氣。 它是煙霧,食物中的香氣和涉及的混合物,但是如果您知道要尋找的東西,就會發現。 “會非法飲酒嗎?” 我想說大概是Palice。 自製? 畢竟,通過在冬季免稅前出售它是一種改善的好方法。”
他們沉默而凝視。 然後,石匠大聲笑了起來,站了起來。 “女人! 將杯子和投手帶出密室。“然後他轉向我。 “您將親眼看到投手上的印章是真實的! 只是真正的州酒。”他敦促妻子採取行動。 “當州葡萄園為我們提供如此優質的產品時,我們應如何開展此類活動?”
“當然。”我揮手。 “原諒流浪的和尚,小惡作劇。 即使是一個有信仰的人,也很喜歡在很少有機會這樣做的時候開心和大笑。 請別怪我。“我吱吱作響,我從葫蘆的喉嚨中拉出塞子,然後向每個酒杯中倒了一瓶金液。 “好好享受!”
雖然每個人都享受著強烈的品味,但他們不習慣,而且他們的印像很簡陋,我瞥了一眼已經放在櫃子上的水壺的眼角。 它上面的印章非常合適。 儘管如此,經常用來生產自製酒精的燒碎顆粒的痕跡幾乎可以在任何地方識別出來。 它是一種結晶礦物質,具有強烈的苦味和香氣。 它燃燒留下的小黃點,特別是在除煙屋頂周圍的木樑上。 畢竟,從我的童年開始,我對這種生產有了足夠的記憶。 直到我的家人被送到了韓國人面前。
正如我保密地告訴他的那樣,我南瓜的精美飲料真的很神奇,她在路上是一個無價的幫手。 它不是管理員的禮物,而是舊配方。 我只是允許它通過幾種方便草藥的混合物來改善,這些草藥的成分我在旅途中一直備案。 在合適的數量,他甚至可以告訴最沉重的沉默,第二天讓他成為一個窗口,他不得不問鄰居他自己的名字。
當樂趣醒來,檢察官的煩惱羞怯從現在消失時,我總是對靈魂感到高興。 當人們互相開放時,這並不奇怪。
為了進一步驅散緊張的殘餘,我開始講述我的起源。 在所有石匠大師第三次用合法獲得的水壺裝滿我們的杯子之後不久。 當我傾訴他們只是在童年時代過早的朝鮮人時,我的聽眾引起了極大的關注。 韓國人沒人喜歡。
校正者就像君主的延伸臂。 它是一名執行官,通常是司法權力。 校正器代表國家的眼睛和耳朵。 它是一個從整個領域提供新聞的信息渠道。 當然,在很大程度上,多虧了它們,它在路上相對安全。 沒有公眾輿論說的那麼多。
帝國是偉大的,個別國家通常有足夠的資源來解決其領土上的秩序,但這還不夠。 如果統治者必須維持他的主權政府,他需要主權。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國家正在巡航男人,有時是女性,她們有權採取行動,並在必要時指揮。 由統治者或至少由他的一名代表授予的權力。 麻煩的是,他們並不總是穿制服,他們並不總是堅定不移地忠於自己的使命。 對一個簡單的人來說,一些不信任只是生存努力的健康表現。
“那你為什麼要加入自己敵人的陣營?”這位大鬍子的農民問,他們說的最少,皺著眉頭最多。
“當我的哥哥和我被遺棄在燒毀的房子里之後,我們的父母被埋葬了。 沒有人幫助我們。 他們很害怕。 當時,我討厭所有人,但是時間變化很大。 我們離開了,並儘了最大的生存能力。 我向校對員發誓復仇。 一個小孩的瘋狂想法。 過了一會兒,我們結成了一個幫派。 只有少數可憐的人失去了希望。 他們偷了他們所能做的,有時殺死了一個人。 但是有一個領導他們。 他帶我們接替了他的父親和我的兄弟多年。 他教了我們很多有用的東西,但最後他卻像其他人一樣最終-遮瑕膏的劍尖。 他們來找我們時真是大屠殺。 他們想殺死我們兩個人。 我的兄弟為我辯護,他當然無法生存,然後只有我一個人了。
我不知道現在有多少名,但其中有一位和尚。 我記得他在我的頭和從高處掉下的刀片之間刺著拐杖。 他為我站起來,說我還太年輕,教堂將確保我以不同的方式贖罪。
“那麼你是怎麼成為和尚的?”很長一段時間後,木匠的妻子說,盯著我,顯然是在關注我的故事。
“是。 我的靈魂找到了安寧,並隨著時間的流逝獲得了寬恕的力量。 儘管這些都是痛苦的回憶,但我不再責怪那些殺了我父母和後來的強盜同伴的人。 畢竟,他們只達到了與我相同的崇高目標。”
片刻寂靜,爐膛裡裂開了幾根原木。 很長一段時間後,石匠的妻子再次講話:“我們都非常感激我們能夠在這里和平生活,我們避免了這種不便。”她微笑著站了起來,並用鎬調整了火勢。 然後她走開了,可能是為了加油。
“我希望它保持這種狀態,”石匠咆哮道。
我笑了。 “這似乎是一個充滿善良和慷慨的人的好地方。”我拿起酒杯,並圈了起來,以紀念主人。 “相信我,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只會為你散佈讚美。”我從玻璃杯裡喝了剩下的液體,站了起來。 “是的,現在是時候!”我從船尾拉出一條鏈,上面掛著太陽的符號,掌心張開,眼睛的中心是我們的主胡拉胡勞坎神的象徵。 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經常叫他草裙舞。
管家剛回來時又在後牆上折疊了幾根原木。 我從脖子上拿起鍊子,抓住我的手,向各個方向親吻和祝福。 我祝福這個住所和其中的人民。 我已經說了一些聖潔的話來吸引神聖的注意力來吸引這所房子並為未來幾年帶來足夠的關注。
午夜一定過去了。 “朋友!”我舉起雙手。 “我感謝您的盛情款待和如此令人難忘的公司,您使我無盡的旅程變得多樣化。 謝謝你,“我向他們每個人鞠躬。
“現在,如果我有一個自由的角落,我將在清晨躺下頭,我再也不會因為我的存在而打擾您了。”
幼崽在隔壁房間被發現。 還有床墊和毯子,這是一種不常見的奢侈品。
在祝公司晚安並再次感謝您所做的一切後,管家說:“我已經準備好一切。” 然後我消失在黑暗中
在四面牆之間,只有少量的月光透過。 他沉入毯子裡,閉上了眼睛。
一整天的行軍和談話都持續到深夜。 我筋疲力盡。 我頭腦中的酒精也沒有太多幫助。 我感到痛苦的睡眠在我身上。 當我經常呼吸時,我聽到了低沉的聲音。
透過狹窄的窗戶只能看到早晨的蔚藍天空。 新鮮空氣流入,寂靜無聲。 我躺在床墊上,只是看了一會兒舒緩的顏色。 我知道我必須起身繼續前進。 我伸了個懶腰,走到窗前,向外看。 我想:“看來他今天旅行得很好。” 我是如此柔順,以至於失去了警惕。 我打開門,進入主房間,然後立即絆倒了有人留在那兒的沉重的原木。
“啊,該死。”我詛咒。 我忘了我已經讓他躺在那兒了,而且以前也曾絆倒過他一次。 我太累了,只是沒有強迫自己整理一下。 實際上,這不是我留在那裡的原木,而是農民。 我想到我要先吃早餐。 清潔將需要一段時間。
晚飯後還剩很多東西。 我的味道只被木匠手上燒焦的肉的味道所破壞,這種氣味在隆起的邊緣進入爐膛時有些令人不愉快地下降。 是我的錯,我沒有註意到。 現在我的眼睛正焦著他焦黑的皮膚。 “我很好,”我說。 我的這部分工作並沒有使我感到絕望。
我嚼著仍不冷不熱的燉家禽,環顧四周,尋找周圍的混亂情況。 “我不會清理牆壁上的飛濺物。”
我受夠了。 我很不情願地將碗放下並拉直。 我的背裂了。 “那麼,和尚?”我問自己。
我雙手叉腰站立,身體被遮蓋。 “我可能會一次把它們拔出來。 還有什麼。“所以我把它們拖到了房子前面。 我只讚賞牧民過去回想過去的嘗試。 他絕對是所有人中最難熬的,他會讓我失望。 幸運的是,他已經在門口躺了幾個小時。 當我翻閱過去一夜的記憶時,我發現我從未見過像這樣胖的牧民。 實際上,他似乎根本不是牧羊人,而是一個屠夫。 只要他能,他也很靈活。 那搖了搖頭。
我對木匠有點遺憾。 畢竟,當其他人談論如何最好地擺脫我時,她是唯一一個反對的人。
“不,”她敦促丈夫。 “這不是必需的。”
“閉嘴,鵝!”他對她嘶嘶地說。
自從我失敗以來已經過了幾十分鐘。 石匠送他的妻子聽她的耳朵貼在門上一會兒。
“我什麼也聽不到。”她小聲說。
“好吧,”他說。 “也許他是一個和尚,也許他所說的一切都是真的。 也許不吧。 但我不會冒險。“他分別看著每個人。
農民拉起他的襯衫的袖子,以提醒其他人他前臂上的深深傷痕,這仍然是在提醒與前一個聖人的會面。 “自從我們殺了一個和尚已經很長時間了。 最後一個也不是沒有防衛的。”
牧民大部分時間都保持沉默,盯著袋子很長一段時間,掛在前門旁邊的一個釘子上。 “我想知道您要存儲什麼。”
木匠說:“我們不知道他來這里之前聞了多久。 當他嗅探到我們要在這裡製作Pálice時,他也可能會注意到另一個人。
“如果我們讓他離開,校對員將很快出現。 很明顯,“石匠總結道。
“我不認為他有危險,”木匠的妻子嘆了口氣。 “為什麼明天再把他留在這裡,好好對待他。 他肯定有熟人。 我聽說教堂向和尚提到得很好的人捐款。 這也將消除人們對村莊里人的懷疑……”
“你怎麼這麼傻!”他的丈夫要求。 她低下頭。 “等一下,我會送你到他身後的黑社會!”
在我到達的門口,管家似乎是一個堅定的女人的印象。 她現在默默地打開插座,拿出一把長刀切根菜。 他的刀刃在火光下閃過。
“是的,”石匠說。 “這次輪到你了。”
胖牧羊人笑了。 “ A,我要砍他。”
“沒人從你那拿走那東西。”木匠沉默了他。
石匠對那個女人點點頭,她慢慢地,安靜地打開了門。
隨身攜帶兩件行李總是好的。 當你讓你的負荷躺在你觸手可及的地方時,人們會安撫,然後往往會忽略你的第二針。 如果你不遠離任何可以用作武器的東西,例如你的旅行棒,它也不會給人留下好印象。 簡而言之,他們不那麼謹慎。
儘管我希望能夠安靜地過夜,但主對你有許多意圖。 一直強迫睡眠很累。 我敦促他們,如果他們想做任何事情,就快點做。 這就是為什麼我對擺動鉸鏈的微弱旋轉感到非常滿意。
但它完全不同。 就在片刻之前,我跳出床墊迅速蓋上毯子,使攻擊者感到困惑,至少乍一看。 我覺得它足夠厚,可以讓它走了。 我作品的深色也沒用。
我背對著窗戶,離窗戶只有一米遠。 陰影最黑暗。 他把頭罩拉到頭上,遮住了蒼白的皮膚。 用我的手,我打開了一個小袋子,我把它放在腰間,拉出我的混蛋。 他把它藏在一個寬袖子的褶皺裡,所以他偶然沒有從裡面的一點月光中反彈而沒有呼吸。
“一個……兩個……三個……”,我默默地聽著腳步聲。
她輕輕地將她蒼白的手臂輕輕撫到蒼白的蒼白溪流中,然後抓起毯子。 刀片白色閃爍。
突然的呼吸和驚喜。 沒什麼。 我的投擲刀的刀片突然進入管家的睡眠狀態。 我盡可能快地趕到她身邊抓住她墜落的身體。 我指示他,讓他默默地摔在床墊上。
將刀鎖在頭骨上是一定的延遲。
“接下來是什麼?”我的頭閃爍著。 幸運的是,窗戶足夠寬,我可以伸開。 這給了我一個優勢,讓我感到驚訝。 我在房子周圍走來走去,壓在前門上。 片刻的沉默。
“她怎麼這麼久?”一個人說。
“去看看吧。”另一個咆哮。 鎬吼,腳步聲響起。
現在是正確的時刻。 在幾秒鐘內,為時已晚。
我打開了門。 石匠先跳了起來,然後跑到了槍架上。 他把它甩了,但他沒有回來。 同樣的刀片推翻了計劃
他的妻子和他的妻子。 他的頂部有一個沉悶的撞擊,然後在撞擊一個巨大的檯面時射擊。
與此同時,木匠靠在牆上,但偷獵者走了。 只留下灰瓢。 他像一個俱樂部一樣抓住她,直奔我,跳過板凳,把妻子扔到地上。
我能伸手可及的唯一武器就是我的棍棒,它一直在耐心等待。 我伸手去抓她,用刀片彈了第一擊,另一端擊中了後面的男人。 他畏縮了一下,但再次受到了攻擊。 我抓住我的手,好像我想把她撕成兩半。 一條長直的刀片從她身上溜了出來,棍子的末端是她的刀柄。 我很驚訝。 Tesar的決心很酷。 但為時已晚。 我左手的棍子底部擊中了他的臉,在失去平衡的同時,劍的刀刃從左側穿過它到右肩。 就在那時,他的手進入火焰並開始烤。
與此同時,農民已經能夠從他的發現任務回到我的臥室,並把我扔到了我的身邊與肥胖的牧羊人。 我沒有註意到他來到他身邊的地方,但霹靂手裡拿著一把菜刀。 大菜刀。
我對他們立刻反對我的想法感到有些失望。 我揮動劍,釋放了我的手掌。 細長的金屬帶在空中尖叫,穿過胸骨下方的農夫。 另外,我認為我猛烈地向他投擲,迫使奔騰的人朝飛行方向並將他釘在木門鈴上。 從技術上講,這是一個錯誤,不僅我自願解除武裝,而且如果它擊中了牆上的石頭邊緣,我也可以摧毀我的武器。
我的鑿子經過好幾次。 在那里和後面,來回。 我像我一樣跳了起來。 我用棍子的剩餘部分踢了一拳,但我只是花了一些時間。 我必須得到我的劍。 當我站起來退卻時,我試圖將他的右手放在他背後的某個地方。 它做到了。 我扔了一把劍,武器鬆開了,被釘住的身體滑到了地板上。 它在它後面的牆上留下了像slu slu粘液一樣的血腥污跡。
不知怎的,我轉向了直升機。 我不知道怎麼回事。 然而,突然間,他朝不同的方向起飛。 她的手飛了過去。 攻擊牧羊人開始尖叫並逃跑。 司法官把他趕到了房子前面。
突然間沉默了。 我站在大身體上方環顧四周。 那是一個寒冷的夜晚,星星閃閃發光。 我滔滔不絕地抽出一口清新的空氣。
有一個木匠在房子周圍爬行,可能正在尋找鄰居中最尖銳的東西。 她找到了,但她胖胖的手拒絕讓他離開。
我回到了房子裡。 我擦了刀片,找到了我在長凳邊緣找到的一塊布。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她。 她嚇壞了。 當她顫抖時,她幾乎沒有站起來。 她用兩隻手握住她的前臂,她在她面前揮舞著一根手指如此堅硬的鑿子。 她因血而貧窮。
我靠在櫃子上。 “我想我可以安排他們從總部給您一些補償。 除非,當然,除非有人開始在這裡窺探,然後發現房子後面的被埋屍體。 還有鼓。 但是,如果有人作證對您有利,您就可以輕鬆擺脫它。 畢竟不是你的房子。 您甚至可以為那些屍體辯解,但他們可能會提出很多問題。 所以呢?”
她正在看著她身邊的觸發器,很明顯她無法思考。
“你叫什麼名字?”我問。
她猶豫了。 然後她結結巴巴地說:“露西米娜”。
“你看起來像個好女人,露西米諾。 當其他人想殺死我並切片時,您為我站起來。 你有孩子嗎?”
“兩個。”她的眼中湧出了淚水。
我想。 “當我到達最近的警察局時,我可以發送一條消息,說您在緊急情況下為我提供了幫助,並要求為您的孩子錢。 當我編造一個故事,而你向他們作證時……”
“不!”她大喊。 他們會問:“校對人員會來的。 人們因為我們的丈夫而不喜歡我們。 他們在談論關於我們的可怕事情。”
我打斷說:“我想這裡發生了可怕的事情。”
“我不想,他讓我參與其中。 我們沒有什麼可生存的。 但是他們會背叛我,孩子們會帶我走!”
“可能是。 但是校對人員不會來。”
但是,儘管我嗚咽和絕望,她幾乎沒有聽到我的聲音。 他們可能對此不好。 很明顯,如果有人真的開始問,儘管我
她不會收到任何錢,孩子們可能會把它帶走。 罪犯的孩子得不到好的待遇。 當然,如果......我想到了它是怎麼出來的。
“你在乎你的孩子多少?”
有那麼一刻,她對某些事情感到很瘋狂,但我最了解這一點。
“我將確保他們過得愉快。”
那可能是一個誇張的陳述,所以我糾正了自己,“好吧,至少他們會有未來。”
我覺得他再次聽我說,或者至少是在試著。
“但是我必須做它所需要的。 你也是。 在這裡……,“我伸手向後兜里,掏出一支鉛筆和一張紙。 “你能寫嗎?”她點點頭。 我把他們放在她前面的長凳上,告訴他們在那兒寫下孩子的名字和生日。
她花了一段時間才最終用一把菜刀放下她的手並開始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腳本非常震動,但可以閱讀。
“謝謝。”我說。 我走近她,跪在板凳前,倚在紙上哭了。
“您的孩子將得到照顧。 不用擔心它們。”
她用那些血腥和紅眼睛的眼睛抬頭看著我。 有完全難以理解的希望。 我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刀片盡可能地深入。 她沒有喊。 她呼吸,把頭放在板凳上。 在她的膝蓋之間,一個密集的水坑立即開始形成。 看起來很奇怪。
我拿了名字紙,盡量不把它們弄乾淨。 然後我不得不再次清理劍。 上次。
現在,我可以輕鬆地編輯她的報告了。 派他到命令中最近的城市,並要求該州接管這些孩子。 多虧了他們母親的英勇行為,他們親自殺死了其中一名罪犯並拯救了我的性命,他們才真正有機會。 幸運的是,我知道我的報告本身俱有足夠的分量,沒有人需要進一步調查。 其中一個可以成為僕人,士兵,神職人員,或者甚至可以像我一樣-校對員。
然而,看著我周圍的觸發器,我以為我寧願成為我成功的僧侶。 至少,不時。 我好累。 這麼多。 我打了個哈欠。 他開車回到自己的臥室,第一次偶然發現一個農民在門之間伸展。 把死去的管家從他的床上拉下來是一項超人的任務。 我只是扔了一張床墊
他讓她滾到角落裡。 我站在旁邊,一直睡到凌晨。
當我把所有六個身體整齊地分開時,我抵制了簡單地燒掉它們的衝動。 一般來說,我不喜歡做出決定。 我試著在房子裡搜索了一會兒,如果我找不到必要的工具,我會點亮它們。 不幸的是,我發現了一個水桶和一把鏟子。
我發現將它們直接埋在房子前面很方便。 不深。 然而,當我完成時,太陽仍然在天頂。 這是一種解脫,因為被燒傷的手在新鮮空氣中聞到了,切碎的手也開始傾向於。 儘管如此,蠕蟲和其他寄生蟲在它們發現它之前並沒有花很長時間。
我畫了一些低矮的土墩,為她的可憐女士做了一個簡單的桌子,她的名字和希望安靜休息。 我祈禱他們的靈魂不受干擾的旅程通過黑社會和成功回歸創造者。
剩下的就是在門口向過路人和可能的倖存者留言。 我做了一個金色,其成分屬於道路上每個校對員的必備裝備,並在前門上寫了一個官方標頭,上面寫著:“憑權威的權威”隨後簡要描述了犯罪以及被告和定罪的人。 然後只是警告想要破壞銘文和日期的破壞者和其他顛覆性分子。 最後一行照常讀取:“執行者:OdolakBulahičr旅行校對員。”
最後,我附上並染上了一個官方的金屬模板,上面印有國徽和訂單標誌,這些標誌是我送去旅行的。
它完成了。
在我離開之前,我搜索了箱子,櫥櫃和抽屜,但除了較小的食物供應和放在食品儲藏室蓋子下面的瓶子瓶外,我什麼都不需要。
我只吃了一頓飯,但是在埋葬的時候總是很明顯,但我不想採取艱難的一步。
他度過了愉快的下午。 在斜坡右側的山坡下,我看到了一條細線遊覽。 它肯定會帶我到最近的村莊或
城市。 這就是我將信息發送到總部的地方。 當沒有任何事情發生時,幾個星期內,新鮮的孤兒將會前往Tukatu。
然後也許我將能夠回到我的主要任務並向西北方向轉向我的步伐。 我很高興我的一點點延遲讓人覺得有些東西對他有用。 終於沒那麼糟了。 而且我通常喜歡對在美好社會中度過的快樂時光的記憶感到高興。
續: 關閉會議